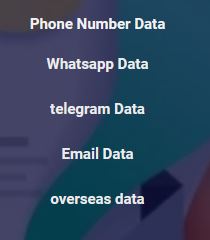考虑到第一个结果,应该为欧盟公民的(非欧洲)家庭成员保留什么类型的保护,他最终是否居住在我的出生国,但被转移到他国家的另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论的是任何由于劳动合同而被迫定期和每天流动、以跨境方式流动的人,他们的生活依赖于可能来自第三国的家庭成员的贡献。然而,这一假设(C-457/12)同时比前一个假设更为复杂,尤其是如果考虑到主体的惯常居住地这次与自由流通的关系不同。因此,欧盟公民的“个人情况”最为重要,包括确定法庭的解释。事实上,正如欧洲法律所规定,欧盟公民属于《欧洲联盟运作条 牙买加电报号码数据 约》第 45 条所保证的工人自由流动的适用范围。鉴于此,公民的“性质”不同,公认的保护程度也会不同。具体而言,如果欧盟公民的家庭成员是第三国国民,并且惯常居住在其原籍国,但经常以工人身份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则可以在该原籍国获得“衍生居留许可”。每当可能的拒绝会损害《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 45 条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时,就必须采取这一措施。在这方面,欧盟审判法院将国家第三方拘留联盟公民的事实列为其中的原因之一。应,对案件进行审理,逐案验证药物的有效“威慑特性”。
总之,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效的例子,说明欧洲公民身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为有效实施某些形式保护的更常见的媒介。此外,司法法庭的这些裁决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情景,概述了该机构可能给外国人的法律地位带来的变化。事实上,尽管这个话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涉及我的成员国的宪法,但显然,根据外国人的国籍和参与社会的形式,存在着具体的“差异”。用本哈比卜的话来说,欧洲血统的“他者”似乎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外来人,因为他在某些情况下承认更广泛、更明确的保护程度,其中还包括在行使某些权利时可能存在的“威慑因素”;另一方面,与欧洲公民有关系的非欧洲个人仍然可以根据其国籍“稳定”其法律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毫无疑问,家庭成员作为家庭环境的“监护人”,除了可能存在的监护子女和年幼子女外,还必须受到比其他成员更强的保护。在所有方面,我们都创建了足够多的问题来重申时间标准(3 个月)以确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系”。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