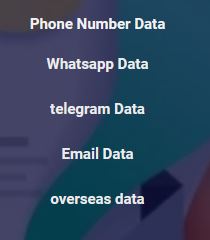盎格鲁-撒克逊公平法并非史无前例地进入我们的法律体系,而是在实践中,受到某些法理学结果的批评者所谴责的人类尊严的运用,越来越像一记重锤,猛烈撞击“法律形式”,直至其“规避”的极限。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例如,2010 年 1 月 13 日萨勒诺法院的命令。长期以来,旨在对备受诟病的意大利 PMA 法进行渐进式的、可以说是“宪法化”的陷入困境的法理学工作的民事(gu Scarpa)可能代表了最先进的(并且首先是讨论过的)前沿[22] :但是,甚至指责法官逐步扩大具体的规范活动具有反民主性质,理由是它会大大推翻民主的基石,即使对于那些指出通过对基本宪章和超国家宪章进行相应不当的“公开”解读来不适当地强制执行这些原则的 黎巴嫩电报号码数据 人来说,客观上也是太过分了(如果不是非常有用的话)。
例如,在临终关怀领域,普通法和民法法院确实倾向于“对那些出于同情心、以或多或少表达的公平需求(即生物公平)的名义,做出中断亲人生命的行为的主体采取有利的解决方案,或者,无论如何,使系统恢复整体合理性” [23] ,但对意大利法官合法性的指控,例如通过参考外国立法和先例(据称缺乏法律效力)“不当使用”比较方法,不能不导致,正如康蒂明智地做的那样,对根据第 14 条对法官规定的法律服从的相同约束进行进化的重新思考。 101 成本:至少在当前这样的背景下,法律的逐渐模糊化深深地标记着宪法和仍然被称为创建一个体系的文件的充分优势。
尽管法官的判决不可避免地受到法律的传统、个人的文化传统或个人良知的制约,但它绝不会像风中的风筝一样随波逐流:相反,它必然会遇到一系列适当的“平衡力量”(即使不能最终平息,至少也可以)来抑制那些针对持续存在的司法任意性风险的最严厉和最激烈的批评。因此,特别是上诉制度所代表的坚实而有力的保护网络、最高法院的规范功能、宪法法院所确保的宪法与规范体系的整合、学说和舆论的审查,以及纪律正义本身,承担了维护最低限度背景的任务,以便法官的科学与良知的交织不会转变为仅仅是个人武断的反面。简而言之,立法的传统作用不但不会被剥夺,反而会因为我们的法律体系中先例的约束而得到合理的加强。 现在,我们已经放弃了旧有的观念,即在这个问题上,现存法律和生活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前者继续扮演着最大的角色,而后者则被降格到灰色和辅助的角色),只有对称的观念才能恢复——如果作者的思想没有被误解的话——现代议会/法官辩证法在“疑难案件” [24]方面真实的、不扭曲的形象。对称放置生命法则,当然,但生理条件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